 同辉学校学生协作查找信息
同辉学校学生协作查找信息
学生有了“迎难而上”的勇气和思路
第1天上午的任务是通过网络搜索和计算推理等方式解决8道题,规定时间内完成。成都市青羊区哪个学校绿化面积最大?青羊区所有初中一共有多少篮球?孩子们看到这样的题目,一下子傻了眼,一旁的老师也开始着急。
本次实训活动导师江学勤却很平静地说:“我手里即使没有标准答案,也能上好这堂课。我会根据他们的逻辑、方法、证据来判断谁更合理,而不是只看结果。”另一位导师张善依也提醒老师们,只给孩子提供安全、工具的支持,不给任何提示。
“学生遇到困难最先想到求助老师,我们要打破这种思维。孩子只要想到一个点,能发散的东西很多。”江学勤说。
“泡桐树小学绿舟分校,根据官方公布的面积,它在青羊区属于前几名,加上它的位置紧邻绿舟生态公园等生态区域,又以田园校园为特色,它的绿化面积应该最大。” B组学生找了多种依据来论证答案。而同台切磋的教师组拿出了教育局“内部”数据,发现与孩子们的推论一致。
当然,面对“哪所美国大学中国学生最多?买一张火车票,从成都到巴黎,最多经过多少国家首都?”这些理不出头绪的问题,孩子们的困惑依然很多:“网上的说法很模糊,难以查到确切数据。”“用电话求助,但对方(餐厅服务员)不配合。”……
当孩子们抛出困惑时,江学勤一改平时“你自己负责”的态度,仔细倾听,并及时回应:不确定数据真实性,就用不同信息渠道相互印证,不能直接找到答案的可以用“逻辑推理”间接得到。合作——分享——指导——再合作,孩子们将集体智慧、老师的智慧都内化成每一次的行动,完成了这些看似不可能的挑战。在老师组多次使用“教育局权威数据”的情况下,最终B组学生仍然赢得本环节最高分。
有老师疑惑,这些问题对初中生来说是否太难?江学勤认为,问题的难易把控在教师手中,答案并不重要,过程中学生学到的信息收集、分辨、归纳与使用,解决问题的思路和方法等才是课程的目的。
逻辑和清晰的表达是核心素养
“你这个思路有问题,而不在于结果如何;你们这组的问题是不协商,不懂得如何清晰表达。”这是江学勤在学生分享时说得最多的话。
在第2天的任务中,涉及简单的计算机编程和小组课题研究。“假如0011+1100=1111;那么0101+0101=?”新加入的同辉(国际)小学五年级组一时摸不着方向,没看懂。本报直播间有老师留言也直呼:“感觉我们真的有差距。”
初中生3个组还在抓耳挠腮或干脆放弃之际,同辉小学的孩子们却并不畏难,通过网络查找、分析和求助计算机老师,率先站出来分享自己的成果。
江学勤很欣赏同辉学校组的团队合作效率和面对困难的勇气,但他同时也直指其问题所在:表演气过重,未真正理解计算机语言。参与活动的同辉学校教师莫影同样有此感受,“B组(同辉学校)只是查找到概念直接念出,不如初中孩子有自己的理解。”
虽有老师表示,对小学生和初中生,这是不是太难了。但江学勤不为所动,活动仍按预设推进。
作为出题人,江学勤说,西方教育中逻辑是基础。有了逻辑,表达才更清楚和简洁,团队中遇到意见分歧也可以诉诸逻辑而不是情绪。学习计算机语言就是很好的逻辑训练。
逻辑训练的目标贯穿于活动始终,如第1天的8道题中有“成都市青羊区哪个小学校园里的树最多?” B组的答案是海滨小学,理由是学校占地面积大,通过同学又了解到学校的植树面积。江学勤马上指出其逻辑不通:仅凭同学一面之词,没有了解其他学校。A组学生紧接着“补上一刀”:这个学校不是青羊区的。
当天下午的任务是寻找举着“我爱青羊”标识的人的照片,背景是创客空间+3D打印机等12个。学生需要求助亲友和陌生人。任务目标关涉如何与人沟通和表达自己的需求。A组力压上午的冠军B组获胜,原因在于该组学生先自己梳理要点,再给亲友发微信、 QQ等,打电话再次确认对方完全明白他们的求助。
“学生多数时候有交流、交友的需求,却又不敢表达,也不懂得表达的方式。”江学勤说。每次分享发言,他都让学生面对师生,大声说出要点,简洁有力地回应问题,而不要过多解释。
成就团队,也就是成就自己
从准备活动上学生搬桌子搭建工作平台到最后一天做视频汇报成果,没有单打独斗,全是小组协作完成。每项任务,只要组员协作不佳,效率和成果就受损。
“现在的孩子多为独生子女,听不进别人意见,对他人也缺乏信任,即使到了大学也不懂得如何与人合作,然而这又是一个处处需要合作的时代。”活动结束后,江学勤分析说。
第1天下午的题目对学生来说挑战难度最大。因为学生发现光靠自己无法完成,必须找人合作,并且是在有限时间里争取到10个不同省会城市的人合作。活动进行不到一半的时间,上午表现最好的组里有学生直接说:“我已经放弃了”,学生尝试了网上发帖子、陌陌摇一摇等办法发现效果甚微之后,开始退缩。
“你们的问题就在这儿,各做各的,队员之间不交流,怎么能形成团队力量?”江学勤一针见血地指出学生的问题。
最终完成任务的A组学生说,刚开始看到题目内心一样崩溃,但组员迅速协商,打电话、朋友圈求助、信息汇总,求助范围甚至延伸到了澳洲。
比起初中3个组,小学组在3天时间里表现得更自信、更勇敢、更具有团队合作精神。他们不惧失败,勇于尝试,拿到任务后也能迅速分工协作。他们“参战”首日,第一个任务就是识别给定面孔的名字——这些人都与互联网发展密切相关。编号,网络搜索,拍照求助朋友圈,信息汇总,不时即识别大半。
这样的团队凝聚力使他们在第4天的任务中占尽先机。虽然被指出存在思路不清,但规定时间内唯有同辉学校组交出了完整视频作品。
初中组的任务是结合前3天所学,以视频方式呈现学校创客空间的设计方案。经历团队协作不力而导致的滑铁卢,又面临着不少组员出走参加学校社团活动,泡桐树中学3组重新组成一组,通力合作,最终交出思路清晰且可操作的方案。
“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,但是一个团队却能走得很远!”泡桐树中学学生这句经验分享,令老师们纷纷竖起大拇指。就连一直以冷峻分析示人的江学勤也露出了笑容:超出预料,所以,一定要信任学生。
想挑战该项目型学习试题?关注本报微信(教育导报1988),输入关键词“STEM”即可获取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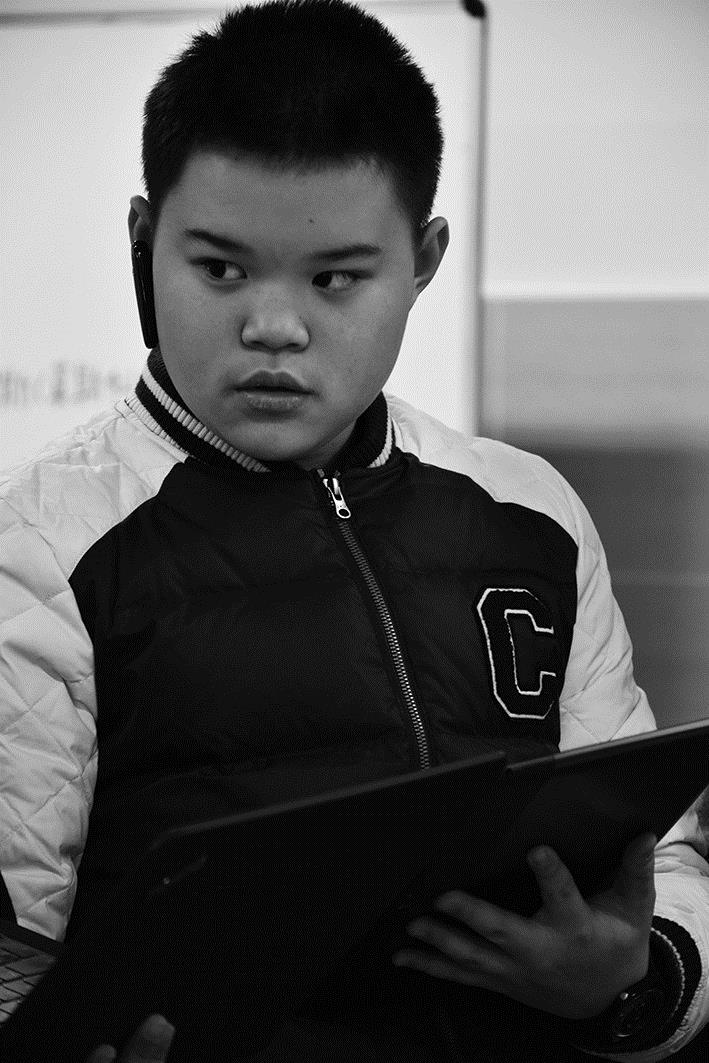
教师思考
STEM教育如何落地?
不少老师全程参与了此次活动,甚至有老师直接上阵组队同孩子们PK。交流发言时,一些老师说出了自己的激动与兴奋,同时也表达了自己的困惑,那就是现有环境下如何实施STEM教育。
孩子们是否真的能独立思考
成都市树德实验中学清波校区教师杨静全程参与了活动,她观察到孩子们在活动中能力得到释放,但她也困惑:信息收集能力是否会使学生养成遇到难题就拿起手机搜索的习惯,而不会自己思考?
“这对老师提出了新的要求,我们自身水平要够才行。”江学勤说,活动中,老师看似没有讲授,但其实从题目设置、游戏规则的制定和指出学生逻辑推理、表达自己想法时的误区,老师都要高度关注。
有老师担心,如果只强调小组内的合作,他们与其他团队只有竞争,是否不利于学生健康成长和培养学生的沟通能力?
江学勤解释说,其实第4天的任务就需要团队与团队之间的协作才能很好地完成。
“项目型学习的问题来源于生活,有助于让学生形成缜密的思维,学会言之有理、言之有据。”成都市青羊区教育局副局长徐江涌说,人工智能的快速发展,我们必须要反思,老师应该教给学生什么?应该是手机不会的。
相应的评价体系需跟上
2016年9月,《中国学生发展核心素养》总体框架历经3年的磨砺和论证,正式发布,引起老师们的热议。如今又引进STEM,如何看待二者的关系?
徐江涌觉得,项目型学习与核心素养可以对接和互补。“核心素养最终要靠行动来体现,课堂教学大多是‘输入’式学习,而学生获得解决问题的能力,未来过上有品质的生活,需要靠行动。”
同辉(国际)学校教师莫影分享了学校的经验。学校“全球学者项目”,每周三下午开课,孩子们围绕吃住行等与生活紧密相关的话题进行讨论,搜索相关资料进行研究,根据研究结果提出解决方案,比如发出一份倡议书,国外孩子也能看到,当孩子们看到倡议书得到反馈时,非常有成就感。
有了好的学习方式,相关评价也应改革,否则,这种教育方式难以调动学校和老师的积极性。
“素质教育、核心素养要落实,教学评价体系需改变,不能简单地打分,应关注过程。”莫影说。徐江涌也认为,引入过程性评价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方向。
小范围推进,用成果去回应争议
不少老师提出, STEM教育看起来的确好,但如何落到实处?要是有可供借鉴的案例和从上而下的推动或许可行。
作为本次活动导师之一的张善依建议,假如你想要改变,就要去尝试和探索。STEM也好,核心素养也好,不去积极应对,适应新的教育理念,绝不可能做好。
青羊区教育科学研究院刘静老师则为STEM教育落地提供了一个框架性方案:1.调查了解青羊区学校现状,哪些学校在做,做得怎样?哪些经验可借鉴,哪些学校有意愿参与变革?2.要取决于老师是否有意愿,校长是否愿意改革,是否有强的执行力;3.要做好相关教师培训;4.学校之间要加强合作交流,要有展示的平台;5.教育局层面,要做短、中、长期目标和规划;6.成立专业测评委员会,将学生项目型学习的成果换成学分,作为升学等的参考。
江学勤认为,有相关意愿的老师可以组成小团队,先以情感为纽带,实行跨学科融合教学;学校层面则提供环境,如建立工作坊等。他并不赞同用一套模式去涵盖所有的教育内容。
专访江学勤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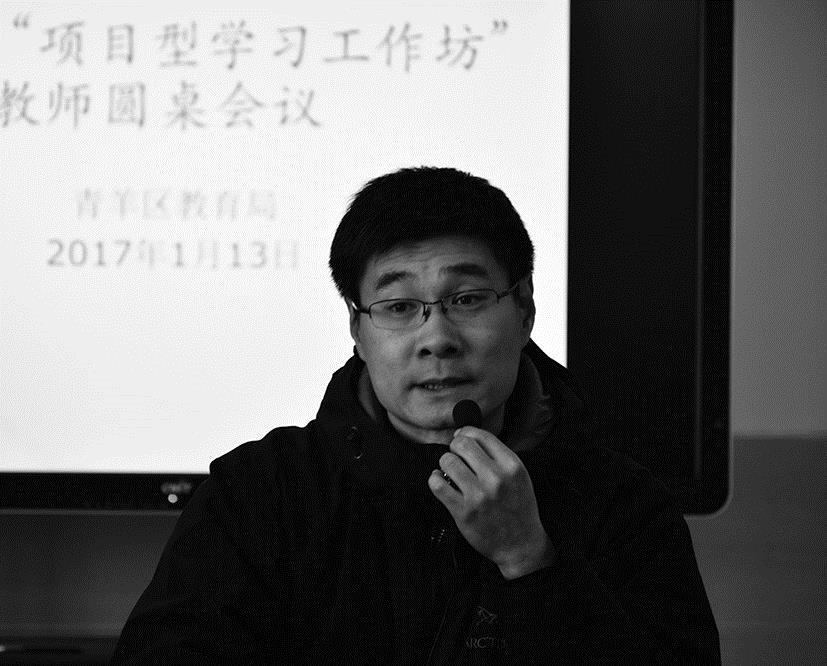
先创造小环境 不要急于求成
教育导报: STEM教育的重要性在哪里?
江学勤:信息时代变化快,对人的能力要求不一样了。自动化步伐的加快,不少原来需要人工的工作,现在都可以用机器人来代替。学习阶段对学生的创造力和想象力要求提高, AI(人工智能)和电脑,全靠逻辑推理。从国家经济需求和整个社会的需要来说,教育方式的改变也势在必行。
教育导报:就路径而言,我们可以在哪方面突破,将传统的教育方式转向STEM教育?
江学勤:我自己也还在探索。我觉得工作坊是一种不错的推行方式。
目前教育环境下的学生,更在乎的是成绩、结果,看重老师和家长的表扬。也就是说,他们更关注外在评价。
这次工作坊实训,即使没有奖励,孩子们仍然乐在其中。人其实有多种需求,需要亲情、爱情、友情,需要他人的认可等,而学校教给孩子的还是太单一。我们更应在乎的是通过这个过程孩子们能获得什么,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结果。
我觉得,学校应该给愿意参与变革的师生创造条件,搭建一个平台,而不是去面向全体硬推。比如,做个创客坊,有意愿、有时间的师生就有了空间和环境,也可以与社会上的创客空间合作。有了这个空间,很多信息就能流进来,交流和联系都会增加。
教育导报:一些老师认为,在现有评价体系内,若对提高学科成绩没有帮助,难以调动大家积极性。STEM教育能否做到量化评价?
江学勤:目前的评价体系难以体现STEM教育的成果,需要寻找新的评价方式。就工作坊项目而言,这是培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好办法,合作、表达、缜密的逻辑思维、面对困难的勇气和方法,这是人增强自身核心竞争力的品质。
实质性参与的家长和老师观念都会被颠覆,大部分孩子能成长为拔尖创新人才,也有一部分参与意识不强的孩子会被“淘汰”,这很正常。因为老师提供的是平台和支持,学生想要学到什么程度需要自己选择。
教育导报:项目型学习突出问题意识,主题化教学,老师讲得少,学生通过玩的方式来学习,是否可能存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问题?举例来说,像历史学科,有断代史和专门史,类似于一个主题学习,但假如没有通史的概念,学生的知识也很成问题,不够系统,思考问题有滑向片面的倾向。
江学勤:项目型学习更偏重工程类学科,在理工科中运用得多些。但确实存在你说的问题。
这就对老师提出了很高的要求。老师看似不讲,但他必须熟知整个项目,掌握目标、方式方法,具备相应的理论知识,不然老师也不可能正确指出学生思维上的逻辑错误,没办法正确引导。
没有好孩子、坏孩子的区别,学生在团队中不配合,是因为他们觉得难,没有方法去沟通,所以,老师要引导,要给他创造成为好队友的环境。
老师的水平不够就难以实施,国外情况虽然好点,但也主要是在大学中开展。所以,活动中老师及时的、准确的评价尤为重要,不能太宏观地去说孩子做得怎样。
教育导报:你能否就课程设置给老师们一些建议?
江学勤:一定要靠近游戏,游戏化、好玩,学生才乐于参与。课程设置时要注重三个方面:好玩,贴近生活,有深度和挑战性。